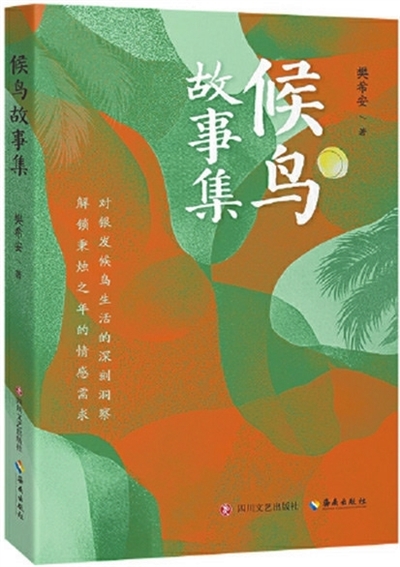○王霆钧
有一些鸟,向往温暖,按季节迁徙,称之为候鸟。有一些人,喜欢温暖的生活环境,每当霜降前后就从大陆成群结队地赶往海南,被形容为候鸟人。这一批又一批候鸟人的到来,让原本平静的海岛喧闹起来,成就了椰影摇曳的别样风景。著名出版家、作家樊希安退出工作岗位后也同夫人加入到这个候鸟人群中,给热闹的候鸟人群增加了几分快乐,贡献出了以候鸟人身份写出反映候鸟人生活的《候鸟故事集》。
这本小说集由4个颇有规模的中篇和7个短篇组成。如果将中篇比作大戏,那么短篇就是独幕剧或者小品,长短各有特色。作家以敏锐的观察,厚实的生活底蕴、丰富的文学积累和联想,为我们写出了候鸟人的生活,描绘出了这些人独特的精神风貌,有爱有恨,有友谊也有爱情。爱恨情仇构成了非同一般的人生戏剧。于是,恩爱的夫妻分手了,破碎的家庭重组了,久别的夫妻团聚了,多年的冤家和解了,怀揣的梦想成真了……
故事集开篇之作《椰岛豫韵》,以候鸟豫剧团为生活场景,以“我”即潘作家为贯穿,以寻找表弟媳妇周小莲为线索,编织了一个生动有趣又环环相扣悬念叠生的故事,最后以大团圆为结局满足了读者的欣赏心理。第二篇《梅兰竹菊》里探讨的异性友谊,却颠倒了原本平静的生活。《掌叔和甩鞭的女人们》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擅长甩鞭子的老汉,独自在海南为儿子看守一座别墅。一手绝活吸引了许多人,男人冲他的绝活来,女人呢,说是向他请教甩鞭技艺实则是想着他住的地方。《老熊与白鸽》写了一对老夫少妻,出乎意料的是老男人突然出走远方,把年轻漂亮的妻子晾在家里……
作为叙事艺术,小说首要的是有个好故事。该书作者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小说发表,作为一个小说的行家里手编个好故事是拿手好戏。然而仅仅有一个好看的故事并不是好作家的本事。如果将好作品比作美女,那么好故事只是漂亮的衣服。作家的笔触要透过衣服深入肌肤挖掘心灵,探索丰富多彩的人性。
《椰岛豫韵》中“我”的表弟媳周小莲痴迷豫剧,弃子出走30来年。什么缘由让她连亲生儿子也舍得扔下?待“我”见到候鸟豫剧团团长高小萍疑似表弟媳时,以作家身份深入进去一探究竟。面对剧团婚姻现状,探讨了婚姻的名与实,将这篇小说提高到伦理层面。接着,作者通过高小萍和师妹付红的关系,揭示了行内“要想会跟师父睡”的潜规则,为了演戏高小萍李代桃僵,甘愿替付红献身。事后她对付红说,“我是为救你,也是为自个学唱戏。戏比天大,我宁可做出牺牲。”高小萍的行为何尝不是一种人性的流露和表现呢。
《梅兰竹菊》写的是婚内男女交往中异性朋友的友情。两个和谐家庭因为一个风流成性的局外女人毁灭了。恩爱夫妻反目成仇,源于一条腰带,深究起来,真的是腰带惹的祸吗?100个读者有100个哈姆·雷特,相信每个读者读过这个故事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小说是语言艺术,不能不说到该书语言如何耐读,经得住细品,像陈年老酒,像明前新茶,时不时出现的诗词仿佛鲜花一样装点着这片语言的草原,活色生香,说炉火纯青也不为过。要塑造好人物必须写好人物心理,作家在这点上有自己的创造,展现了非凡的功力,比如,楼上的女士刘素英和楼下的男士杨占义交往的心理过程描写得细致入微合情入理。候鸟小说表现候鸟人的生活,两性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这是难以把握的。可是作者利用比喻的方式把这一难题表现得游刃有余。比如反映刘素英和丈夫在床上,作家将这位风韵犹存的女人的性心理描写得惟妙惟肖,比喻得恰到好处,“自己的机器没坏,只是没适合发动而已?自己不是沉睡的港湾,只要有轮船进入,港湾就会喧嚣起来。自己的黎明也不静悄悄,只要有雄鸡啼鸣,黎明也会市场喧嚣。”这些形象的比喻,作者信手拈来,准确又含蓄,俏皮中透着机智,说“生过孩子就像砖窑,再生孩子就像出窑一样顺当。我这是窑,就看你能不能装上窑了。”两个人想做那个事,暗号就是“装窑”,即使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说,别人也不明白他们说的是啥。又比如,付红和郑虎表示要做到婚姻的名实一致,“我”劝郑虎要少喝酒,以免生个有残疾的孩子,说的却是“封山育林”,二人心领神会。作者的语言,就这样有庄有谐,有雅有俗,庄谐交汇,雅俗共赏。
故事集的故事,不论长短一律以第一人称表现,即使大段心理描写,由于“我”的出现也会有代入感,亲切如聊天,真实可信,似乎都是“我”的耳闻目睹。《老熊和白鸽》,每个人物都是第一人称。白鸽为什么离婚和一个老农民企业家结婚?这个老夫为什么离开少妻远走他乡?其中缘由都是当事人以口述方式交代出来,读者和人物间没有隔阂。同时,几个人物的“自白”,又都是“我”在采访中听到的,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我”的身份也并不是单纯交代情节,对故事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如“我”和市场管理人员交涉,和文化厅官员联系让候鸟剧团有合法身份,用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资金支持,等等。
作者将海南风情风光与小说故事融为一体,自然的、人文的,构成了椰影摇曳下的另类风情。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