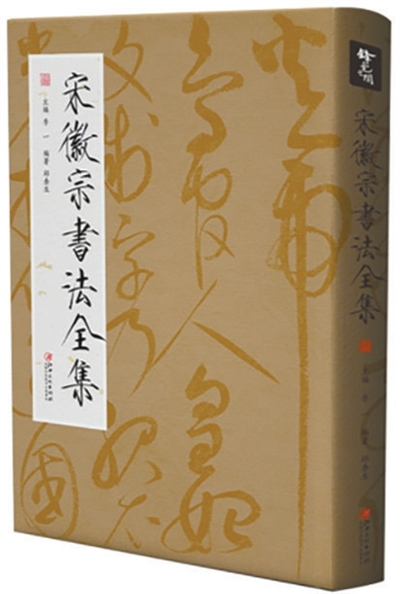○刘 伟
南宋史尧弼言:“恭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宋代实现了从“马上打天下”到“笔墨抒闲情”的转变,进而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宋朝帝王也在不同层面上表现出对艺术的兴趣,其中以宋徽宗赵佶为最。宋徽宗将毕生精力投入书画艺术创作、古物收藏、书画院设立等方面,这与其在政治上的荒废形成鲜明对比,不免使其被后世冠以“艺术天才与政治昏君”的双重身份。元代脱脱编撰《宋史》言:“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宋徽宗特设书画院,著《宣和书谱》,记得当时书家一百九十八人,并各加以评论,为宋代最完美的评书之作。”(王治心《中国书法史述略》)李一先生在概括宋徽宗的艺术贡献时言:他(宋徽宗)引领艺文风尚,振兴书学画院,自创瘦金体,可称一时艺文旗手、千年杰出书家。
宋徽宗书法艺术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书法风格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徽宗早年学习初唐薛曜、薛稷兄弟的书法,汲取了二人书法中的清瘦风格,又借鉴了同时代书家黄庭坚的结体笔法,以“二王”为根基将前人的特色融会贯通,从而“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瘦金体”。宋徽宗草书师怀素和张旭之法,传世《草书千字文》书于十余米长的描金云龙纹纸上,洋洋洒洒、一泻千里。读《宋徽宗书法全集》则可窥宋徽宗书法全貌,领略其独特艺术魅力,打开理解宋徽宗书法世界的窗口。
一序四论、发蒙解惑。《全集》中收录李一先生序一篇,吴彧弓、张耀虎、谢孜菡、杨沆专论各一篇。“一序四论”为读者提供了导读功能。李一先生的《序》提要钩玄,对宋徽宗的艺术地位、书法风格与时代价值等进行了概括。四篇专论则从不同的点展开论述:吴彧弓文章对宋徽宗楷书(即“瘦金体”)的取法渊源、技法表现、美学意蕴等展开论述,张耀虎文章分期讨论宋徽宗的草书及北宋时期的草书发展,谢孜菡文章对宋徽宗“诗书画”一体化的实践创新与审美思想进行研究,杨沆文章则对宋徽宗时期的书学进行探究。通过对宋徽宗的楷书、草书、“诗书画”一体化及宋徽宗时期的书学的研究、论述,为读者勾勒出宋徽宗在艺术上全面、立体的形象。
收录翔实、真疑辨别。《全集》共设置四个板块,分别为“作品”“存疑作品”“其他”“专论”。“作品”板块中收录作品35件,除了常见的墨迹作品,亦收录了碑刻、题签、瘦金体通宝等系列作品。除收录存世且传承有序较为可靠的徽宗书法外,亦单列“存疑作品”板块,收录了《跋李白〈上阳台帖〉》《唐十八学士图》等6件存疑作品。存疑作品多已定为伪作,却可溯宋徽宗书法和后代之间的联系,为探讨宋徽宗书法的传承与演变提供线索。在“其他”板块中,所列“宋徽宗书法年表”则为宋徽宗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梳理出更为清晰的时间脉络。编著邱金生是一位大力推广宋徽宗瘦金体的书家,他对瘦金体研究较为深入,以网络为媒介传播,影响甚广,在《全集》中,《怪石诗帖》便是由邱金生先生手书补填的。
帖刻互参,他山攻玉。在《全集》中收录了宋徽宗《草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残卷)拓本及郁孤台本《草书千字文》拓本,墨迹与拓本在书写的年代和材质上存在差异,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亦不同。墨迹《草书千字文》行笔流畅,于提按顿挫之间表现出宋徽宗的书写才情与艺术天赋。而《草书千字文》拓本的笔画纤细、劲挺,与传怀素《自叙帖》有神似之处,呈现出与墨迹不同的风格特征。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时常考虑书法是否还需要纸质版的资料。答案是:只有翻阅纸质资料方能感受到其意义,对纸质资料的需求本质上是对“人性化需求”的回应。在算法推送所制造的信息茧房中,在被数字设备裹挟注意力的时代,纸质资料可能表达着一种反效率至上的价值选择:尊重人类感官体验的多元性,承认知识传承的物质性,守护文化记忆的温度。纸质书籍让平面的文字、墨迹更具立体的维度。翻阅《宋徽宗书法全集》让我们看到一个失败的帝王也能以笔墨在历史长河中构建丰富多彩的书法世界,领略到宋徽宗赵佶作为帝王书法家的独特才情,感受到“瘦金体”独特的美学价值,体会到“诗书画一体”的艺术魅力以及宋徽宗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与书法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