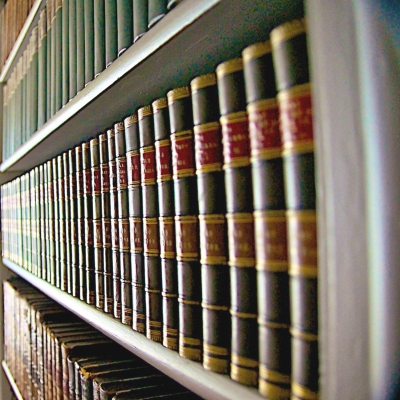不管是不是跟“斯诺登事件”有所关联,曾在国内文学界和影视界刮起一股强劲“谍战题材风潮”的麦家,其谍战文学作品,又开始征服英美世界的读者了!近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从麦家任职的浙江省作家协会获悉,麦家的经典密码小说《解密》的英译本,已由英语世界第一大出版集团企鹅英国总部和美国FSG出版集团3月18日在美、英等21个英语国家推出上市,并被收入英国著名的“企鹅经典文库”。据浙江省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赵国成介绍,“上市仅一天,《解密》就成功打破中国作家在海外销售的最好成绩,冲破美国英国亚马逊10000名大关,当时排名第6102位,在此之前,中文作品最好排名是49502位。”
“我今年50整,才出第一本英文小说,讲起来不是什么光彩事。”说到作品在英美两国上市,麦家颇为感慨,并坦言“更多靠的是运气”。由此,中国作家如何“走出去”,近期也成了业内外关注和热议的话题。
《解密》刷新中国作家海外版税纪录
诞生于1935年8月的“企鹅经典文库”收录了乔伊斯、普鲁斯特、海明威、萨特、加缪、卡尔维诺、弗洛伊德、菲茨杰拉尔德、马尔克斯等诸多大师的作品,其中也包括《红楼梦》、《阿Q正传》、《围城》以及小说集《色戒》四部中文作品。《解密》是迄今唯一被收入这一文库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赵国成向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介绍说,《解密》以15%的高版税刷新中国作家海外出版版税纪录。此前,中国作家海外出版的版税一般只有6%~7%,10%已经是凤毛麟角,而15%不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已达到欧美畅销书作家才有的待遇。
麦家也告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因为题材“敏感”、作者无名,《解密》曾被退过17次稿。“长达10年的修改过程确实太长了,几乎差点把我憋死,这么多修改至少有一半是被迫的。《解密》是我的磨刀石,它折磨了我,也磨砺了我。”
英国汉学家米欧敏2010年从首尔到上海来参观世博会,返程时遇到了飞机晚点,在机场买了《解密》和《暗算》打发时间,对两部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米欧敏把《暗算》的译稿介绍给了她的同学、翻译过鲁迅和张爱玲作品的汉学家蓝诗玲。企鹅兰登书屋的编辑正是经过蓝诗玲之手,接触到了麦家的作品,随后与麦家和他的海外代理人谭光磊签订了出版合同与翻译合同。
中国作家
“走出去
”三途径
今年3月7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刊发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何明星的《独家披露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作品之欧美影响力》(详见本报第2022、2023期合刊第9~10版),其借助日渐丰富的海外数据库资料,勾画出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欧美世界翻译与传播的现状。文章刊发之后,不少读者来信来电咨询:为何一些在国内受到读者追捧的女作家没有上榜,比如方方、毕淑敏、安妮宝贝等。确实,进入前20名的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风靡一时的女作家。近年来,那些在国内比较活跃的女作家反而没有受到欧美国家的关注,让不少人感到特别意外。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欧美国家对中国作家的“别样偏好”。
显然,中国作家如何“走出去”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只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文字介绍到国外,其中有数百位中国作家的作品,这个数字清楚地表明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据一些业内人士总结:中国作家及作品“走出去”一般主要靠三个途径:其一,靠运气眷顾;其二,被汉学家相中;其三,出版机构推介。
汉学家是中国作家“走出去”过程中相当重要的“海外推手”,他们会自己选择一些作品,推介给海外的出版机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作家莫言能够获得诺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的翻译。因为诺奖评委几乎只看瑞典语以及法文、英文作品,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为后者在世界范围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目前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也已经将毕飞宇的《推拿》进行翻译。
此前,葛浩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选择翻译作品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有人推荐作品,另一种是有人找到自己来翻译。他说,最头疼的就是译完作品之后,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让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工夫白费。因此,葛浩文在选择作品时也很谨慎,“我们其实不太在意一位作家在中国的名气,但一定要考虑他将来在美国的影响力,如果不好卖,我们的工作就白做了。”
除了靠运气眷顾和被汉学家相中之外,出版机构的积极推介也是中国作家“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黄蓓佳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海外影响力颇大,《我要做好孩子》、《亲亲我的妈妈》等作品在法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都大受欢迎,她的幕后推手是江苏少儿出版社。据苏少社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能让旗下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顺利地“走出去”,该社构建了版权贸易和儿童图书对外推广平台,与全球多个国家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比如,《我要做好孩子》的法文版和德文版采用了“双翻译”的形式,即让一个法国人和一个中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共同参与翻译。中国译者提供文化背景知识,外国译者将这些内容转化为目标语言,以弥补单人翻译在文化背景方面的不足。
作家及作品“走出去”离不开政府助力
在出版界曾流传着一个著名的故事:早在2004年,原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位领导到法国考察,走在巴黎大街上时遇见了一位法国老太太。偶然搭讪,老太太问:“你们是日本人吗?”回答是中国人,老太太直摇头:“不对不对,中国人脑后都留着一条辫子的!”这位领导深受触动,回国后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这么多年,我们总在向国外输出传统文化,输出辫子、胡同和小脚,直到今天,西方人印象里的中国还是百年前的中国。而当代中国在很多西方人那里几乎是一片空白。会议最后达成共识:必须加强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产品输出。比如,由国务院新闻办、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组织实施的图书出版资助计划——“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为不少作家及作品走向世界带来了新的机会。
又如,2010年“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开始启动,经过此项政府项目的助推,我国新闻出版产品成功进入国际知名图书连锁机构,一批优秀外文图书已经逐渐进入法国拉加代尔集团的3100多家国际书店销售网络,近万种图书通过“全球百家华文书店中国图书联展”被推介到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
其实,作家及作品“走出去”离不开的政府助力并非中国独有,作家邱华栋在一次学术研讨会曾讲起了这样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早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崛起的时候,日本政府拨出专项资金,请来西方的日本研究专家,翻译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等一流作家的作品。这些西方专家被安排住在日本,让他们了解日本生活,观摩相扑、茶道等各种日本特色的东西。由此,将这些日本作家推向了世界,日本出了几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与这种推动方式不无关系。至今,日本仍然有资助外国人的出版计划。无论哪个国家的人,如果要写一本关于日本文化、日本社会的书,都可以到当地的日本使领馆去申请一笔颇为不菲的资金资助。
这些细节看似琐碎,但却也是推动作家及作品“走出去”的一种好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