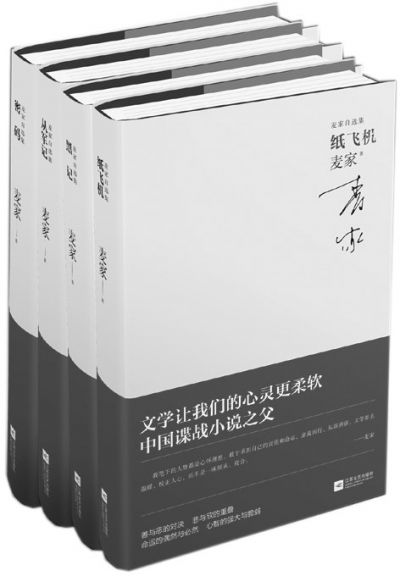麦家的作品在海外出版之前,国际媒体已经开始广泛关注和介绍这位中国谍战小说作家,其中《纽约时报》更是以《中国小说家笔下的隐秘世界》进行大幅报道。这对中国作家来说,非常少见。
除了作家作品魅力之外,还因为斯诺登事件,国际媒体开始关注间谍这样一个隐秘群体。纽约时报更称麦家为“中国间谍小说家”,不过,麦家本人并不认同,他说:“把我的书跟斯诺登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很高明,也很贴切。毋庸置疑,斯诺登和我的主人公干的是同一件事。”他具体解释说,“《解密》中的主人公容金珍和斯诺登是同一种人,都是为国家安全这份至高神职修行、异化的人;不同的是,前者为此感到无上光荣,情愿为此自焚以示忠诚,后者恰恰相反。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背靠背,注定要在两个心向背的世界里扮演着一半是英雄一半是死敌的角色……我不会站在容金珍的角度嘲笑斯诺登,也不会以斯诺登的目光去鄙视容金珍。”这种济世情怀不仅体现在麦家的回答中,在他的小说行文中,也有不停的流露。天才不再是破解密码的机器,他们有了更深广的意义和内涵,那就是他们首先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正如2008年麦家被授予茅盾文学奖时的获奖评价所言,他“书写了个人身处在封闭的黑暗空间里的神奇表现……与此同时,人的心灵世界亦得到丰富细致地展现”。
麦家在小说中对天才下了无数次的定义,在《陈华南笔记本》中他说:“破译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他为我们塑造了瞎子阿炳、数学天才黄依依、陈二湖、容金珍和“捕风者”林英、李宁玉等一系列具有非凡禀赋、才情、思维和意志的人。不过,天才之禀赋既成就了他们,又毁灭了他们。麦家更多的是将目光投向了天才最隐秘的内心,去了解他们内心最隐秘的那根弦,那个能够触痛他们、毁灭他们的内核,在这一意义上超越了语言文字表达与叙事的极限,而这些东西才真正考验作家的功力和小说技巧。天才存在的人生缺憾和命运短板绝对比普通人来的更甚,麦家抓住了这最具有张力和让人扼腕叹息之处,并使他成为了中国谍战小说之父。
麦家曾反复提到影响他的两位作家,博尔赫斯和塞林格。麦家和博尔赫斯有共通之处,“逻辑”、“抽象”、“时空转换”、“记忆碎片”……看似不关联的片断与假想猜测在时空中来回转换,神秘而漂移,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但具有无比坚固的逻辑,可以说:他们在真实和虚幻之间,找到了一条共通的道路,并且走向了光明。但正是由于这样繁密的结构逻辑之辩,麦家需要不停改写和推翻自己,回顾创作,麦家发出过苦行僧般创作的感慨。
麦家多次提到《麦田里的守望者》对自己的影响。麦家出生在浙江一个农村家庭,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他的童年几乎没有朋友,父亲是右派,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没有人愿意和他玩。他只好写日记,把日记当朋友。他的第一篇小说《私人笔记本》,几乎就是他从日记簿里剪出来的。包括后来的《陈华南笔记本》、《解密》等,麦家笔下有一系列笔记本出现,连他笔下的人物都那么爱记笔记,这些记忆的碎片通过现实与想象逐渐构筑成了一个坚固的逻辑长城,形成了麦家的谍战王国。
谍战的动魄惊心在于未知,前一秒还活跃的生命,后一秒就踏入了死亡的深渊。在现实的波诡云谲面前,高尚与卑贱、善良与罪恶、悲伤与欢乐、人性与兽性、成功与失败……一切都那么虚幻。从他的短篇小说来看,《从军记》属于军事题材,如果没有对日常军营生活长期的生活经历,无法把一个农村出来的军人的心理刻画的细腻生动。《纸飞机》通过一个不那么聪明的孩子的视角将悲剧无限的扩大和延伸,使偶然和无奈成为一种必然的不可避免。《胡琴》通过对一个执著痴情软弱的女子华玲的塑造,折射出了人性的卑鄙与疏忽。《黑记》则通过一个特殊的生理特征引出一个离奇的故事,从多种角度对人性进行了描述和刻画……在麦家笔下,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不同类型的人物和故事,但都有一个共通的东西,那就是坚固的逻辑性和推理性,由一个个片断一个个佐证所证明的人性虚无和俗世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