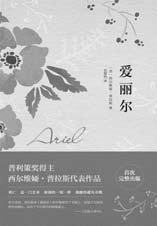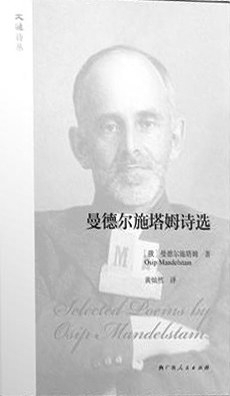作为最美的语言,诗歌曾经有过任何文字表达都无法比拟的辉煌和繁盛时期。海子的名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曾经家喻户晓,然而,那个人人读诗、全民皆诗人的诗歌繁盛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那个缺衣短食的1980年代,诗歌曾经陪伴和激励过一代人的成长,而随着北岛、舒婷等最后一批“朦胧诗”代表在文坛的集体隐退,诗歌的阅读和出版日渐式微,到如今,如果有人说自己是诗人,大都会引来路人的另眼相看。然而,2015年对于诗歌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2015,诗歌的不平凡年
2015年开年伊始,湖北女诗人余秀华的网络走红及其引发的诗歌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犹如给诗歌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自此之后,有关诗歌的各种研讨会以及朗诵会纷至沓来,紧随其后的是诗歌出版的小热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余秀华的两部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和《摇摇晃晃的人间》(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相继面世。抛开各种争议和热炒,对一个诗人来说,这或许是社会给予她的最大肯定和回报。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透露,《月光落在左手上》在面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已经印刷10万册,并预计还要加印。这在近30年的诗歌出版史上,不可谓不是一个异数。
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女诗人,作为一个农民女诗人,余秀华的诗歌为何能够得到社会的如此青睐和热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关余秀华诗歌好坏的热议和争论,一直持续至今,但最终也没分出个伯仲来,有人说,余秀华的成功得益于其自身的各种机缘巧合以及始作俑者的炒作;也有人说,余秀华的诗歌就是好,中国根本不缺诗歌阅读者,缺乏的是好的诗歌和诗人。笔者姑且默认后一种解释吧。诗歌的春天果真要来了吗?或许只能拭目以待。
相比于余秀华,另一个农民工诗人许立志就没那么幸运。许立志生前曾是富士康公司的一名流水线工人。2014年9月30日下午近2点,90后许立志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17层一跃而下,10月1日0点0分,他预设了定时发送的一条微博“新的一天”,准时发布于他已辞别的这个世界的新的一天。其诗集《新的一天》(作家出版社,2015年)之书名即来自于他写给人间的这最后一句话。这是许立志的首部诗集,汇集了作者2010年以来所写的近200首诗,其中大部分诗作是其在富士康打工期间内完成的。在艰辛的打工生活中,在劳碌的流水线生产操作之余,他一直坚持颇具水准的诗歌创作。他的诗朴素、斩截而又强烈,兼具抒情性与批判性,常以荒诞的或令人震惊的笔触书写悲辛的底层生活与幽深的死亡诗意,以此来为2亿多命运的同路人立言,为底层的生存作证。
他们用生命捍卫诗歌和尊严
艺术家也包括作家总是一些异类,他们身上有一种神秘的特质,从远处看,绚丽夺目,缤纷斑斓,造成了他们作品非同凡响的品质。但赋予他们作品奇异的精神元素同时也影响着他们精神的歧义。在他们的精神中,天生有一种普通人不具备的素质:疯狂、迷幻、极度的忧郁或痛苦、不能控制的激情、专注于自我、幽闭或狂躁等等。纵观古今中外,那些一流的作家和艺术家,似乎都处在一种精神崩溃的边缘;有的则直接走向精神崩溃的深渊。有研究表明,心理的异常正是造成他们作品非凡的根源。无论是许立志的纵身一跃,还是海子的卧轨平躺,亦或是西尔维娅·普拉斯拧开煤气的一刹那,他们都是因精神崩溃而走向生命终点。对于他们而言,死亡正如普拉斯的诗歌一样:“死去是一种艺术”。
作为美国自白派诗人的代表,普拉斯被誉为继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但她的一生却是个巨大的悲剧。普拉斯1932年出生于美国的波士顿地区,幼年丧父,1955年6月与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结为连理,1963年2月11日,因情感问题在伦敦的寓所结束自己的生命,并在书桌上留下了一个黑色的弹簧活页夹,里面是40首诗作的手稿合集,时年仅仅31岁。《爱丽尔》(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是普拉斯的重要代表诗歌集,完整收录这40首诗,并严格照普拉斯最后留下的手稿顺序编排,原汁原味地呈现了作者当时的心绪。
同为美国著名女诗人,同样是普利策奖得主,毕肖普与普拉斯的命运却完全不同。毕肖普生前就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并得到布罗茨基、希尼、帕斯等众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推崇。毕肖普虽因幼年丧父,母亲入精神病院,童年时期辗转被外祖父及叔伯抚养长大,让她的一生都在流浪和漫游中度过,正因如此她自称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但正是这段奇特而悲伤的成长经历让毕肖普为日后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肖普一生发表的诗作并不多,但几乎囊括了美国所有重要的奖项。《唯有孤独恒常如新》(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是毕肖普最为经典的诗歌选集,其中包括《失眠》《一种艺术》《旅行的问题》《致纽约》等脍炙人口的名篇。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评价毕肖普的诗歌“写作技艺精湛、形式完美,从专业角度看炉火纯青,让人叹为观止”。
美国诗坛群星璀璨、人才辈出,欧洲诗界也不示弱。在西班牙诗坛,塞尔努达的影响足以媲美安东尼奥·马查多和希梅内斯,他是西班牙“二七一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创作生涯是对欧洲诗歌财富的缓慢继承,风格先后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荷尔德林以及19世纪英国诗歌的浸染,堪称西班牙诗坛的“欧洲诗人”。《奥克诺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是塞尔努达的散文诗集,书中追忆了诗人流亡国外的童年、秋日和故乡小城,在文字中重构一个透明的世界,达成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永恒的渴望。
谈论诗歌,不得不提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这位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著名诗人是“阿克梅”派的重要代表,但其命运却颇为坎坷。他长期失业,居无定所,在1930年代的创作高峰时,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两次被捕,长年流放,多次自杀未遂,1937年12月27日死于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集中营,至今都不知葬于何处。他的作品曾被长期封杀,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才重又引起文学界的重视,文集和诗集由多个出版社再版,并被译为多种语言,渐为世界诗歌界关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形式严谨、格律严整,优雅的古典韵味中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文明气息和深刻的道德意识,并具有强烈的悲剧意味。新近出版的《曼德尔施塔姆诗选》(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是诗人兼翻译家黄灿然在长期翻译、研究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基础上甄选出来的最具艺术价值、最能代表诗人气质和水平的诗歌汇编,共收录诗歌100多首,贯穿诗人的整个写作生涯。这些诗歌博采众长,形式严谨,以卓越的艺术表现力、独特的创作理论展现了对“世界文化的眷恋”,被诗评家誉为“诗中的诗”。
除了上述之外,2015年出版的诗歌集还有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芒克诗选》、《韩东的诗》以及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鼻祖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集《林间空地》以及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智利诺奖得主聂鲁达的诗集《疑问集》,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