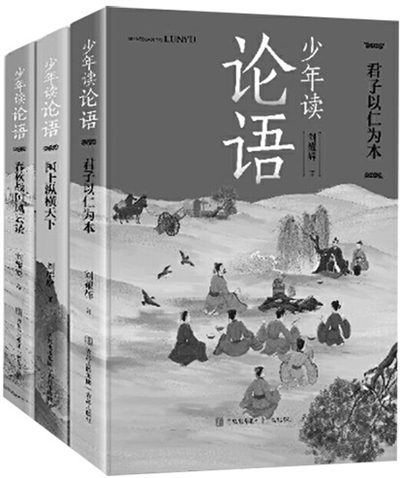○宋华丽
孔子,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说孔子的名字、语录、画像、塑像随处可见,几乎每个人都能来上几句《论语》,儒家思想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中;陌生,因为孔子是神坛上的“孔圣人”,令人仰视,却看不清他的本来面目。
对于当今青少年来说,比背诵《论语》更重要的,是理解《论语》的内涵,汲取《论语》的智慧,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给孩子讲《论语》,作者至少要兼备两项技能:一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对于《论语》有自己的研究心得,而不是泛泛地整合资料;二是能准确把握青少年的阅读心理,能用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把读者带入其中。
从这个角度说,刘耀辉先生是给青少年讲孔子和《论语》的极佳人选。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文史功底深厚,对传统典籍多有研究;他是儿童文学作家,深谙青少年阅读需求,有10余年创作经历,代表作《野云船》《山有扶苏》等多次获奖;他是大学教授,能理解孔夫子的教育观和教学方式,对“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角色有共鸣;他有丰富的少儿图书出版经历,执掌过孔子书房,策划过多部有关孔子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他保持了一颗少年心,多年来持续保持着与青少年交流的热情,所以才有了这部酝酿10年、笔耕3年而成的“少年读论语”系列(共3册)。
该书最大的亮点在于用讲故事的形式,将作者对《论语》的理解文学化、浅白化,生动还原了孔门师生的鲜活形象,向小读者传达了《论语》的丰富内涵,为青少年搭建了认识经典、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桥梁。即便熟背《论语》的人,读到孔门的逸闻趣事也会感到有滋有味。
为了适应青少年的口味,作者的行文不乏幽默气息,可谓深谙孩子们的阅读口味。翻阅“少年读论语”,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两组画面:一个是书中,孔子与子路、颜回等几十名学生或围坐或行走,与学生们讨论天地万象;另一个是现实中,刘耀辉在一群男孩女孩的聚拢中,绘声绘色地讲故事,他乐在其中,而孩子们眨着好奇的眼睛,沉浸其中,不时爆发出会心的笑声。
俯身为孩子写东西,比面向成年读者更需要责任心。“少年读论语”在文学的张扬之外,不失史学的严谨。作者言之有据,除了《论语》,广泛采用《史记》《孔子家语》《荀子》《庄子》《孟子》《诗经》等来源,深入浅出,张弛有度,不曲解,不过度渲染。可以说,作者准确把握了虚构与非虚构的创作尺度。
从今天的角度看,孩子们认识孔子、理解《论语》,能学到什么?
孔子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君子”一词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时让人迷惑。我认为,用今天的话来说,君子教育是一种品格教育,它与学校的知识教育相得益彰。有了健康的品格,青少年在遇到困惑和挫折时,才能不惧一时的艰难,走出浑浑噩噩的“空心”状态,找到前行的动力。
《论语》中包含多种实用的“人生指南”,教给读者不断开创和修正人生,做最好的自己:与人交往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探索学问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制定目标时,“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本人开办私学,打破贵族教育的垄断地位,为平常人打开教育的大门,更是以创新精神为天下人谋福利。这跟当下的教育热词“自控力”“学习力”“积极力”“创造力”等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少年读论语”如同关爱青少年心灵健康的一道营养大餐。在“少年读论语”第一册《君子以人为本》中,作者生动记录了子路从桀骜不驯到尊师好学的变化。面对“三观”迥异的子路,孔子如春风化雨,轻松点拨,使子路重新认识自己。由此,作者在后记中殷切地写道:希望读者“真正理解、接受《论语》的精神,进而在心田为《论语》留一块地方,让它永远住下来,成为你一生的良师益友……”
刘耀辉是与孔子相隔千年的鲁地老乡文人,二人有“浴乎沂”的共同经历。从这个角度说,“少年读论语”是两位鲁地思想者的隔空对话,也是两位理想主义者心灵碰撞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