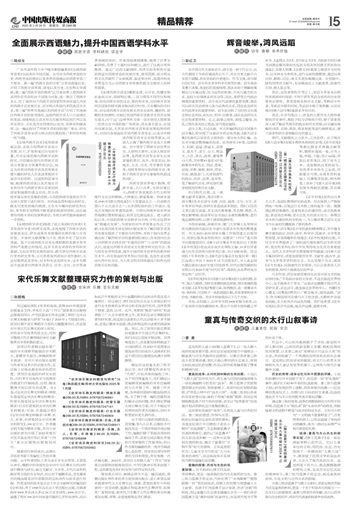○彭红卫
在中国古代文章体系中,诏令是一种下行公文,由古代朝廷下令给臣属或告示天下,其在历史文献中占有很大篇幅,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作为文体,诏令源自《尚书》。诏令具有多学科学术研究价值。诏令常涉及重大决策,是皇权的直接体现,借此有助于理解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权力运作的机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皇权与官僚体系的互动等,因此,是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料。诏令是古代法律的重要来源,借此可以研究其法律效力及与法典的关系,因而也是研究古代法律史的重要资料。诏令还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观念和社会风俗,如礼仪、科举、宗教等,因此也是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总之,政事之枢机、制度之嬗变、治乱之得失及风俗之更迭,皆可借此窥探。
诏令之美,无过汉唐。宋人所编《两汉诏令》《唐大诏令集》,即呈现了汉唐诏令的总体风貌。《唐大诏令集》是唐代以皇帝名义颁布的一部分命令的汇编。由北宋宋敏求整理编录而成。此书原有130卷,包括帝王、妃嫔、追谥、册谥文、哀册文、皇太子、诸王、公主、郡县主、大臣、典礼、政事、蕃夷等13大类,其中第83卷至127卷政事类中的礼乐、刑法、恩宥、官制、举荐、按察、制举、贡举、田农、赋敛各门,关涉到唐代的政治、经济、法律、选举等,是了解唐代历史、研究唐代典章制度的珍贵历史文献。
但自明代后期,这一重要文献多有散佚,现存《唐大诏令集》各本在诏令文题、内容、段落、文句、文字、系年等多有舛误,给研究者造成诸多困扰。同时又因其文多以韵文成篇,其文词古奥难懂,其名物、典故、人物生僻难晓,故亟须对全书加以全面校勘整理,进行笺注阐释说明,以便于读者阅读研究。
为弥补缺憾,泽被后学,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在庆教授担负起对此书进行全面系年校笺的整理重任。作为2021~2035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安徽省“十四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唐大诏令集系年校笺》(以下简称《系年校笺》)是由吴在庆先生领衔主编、10多位学者通力合作共同参与的学术巨著,共计4辑30册。经过团队7年多的努力,《唐大诏令集系年校笺》(第一辑)已由黄山书社于2023年12月出版发行,并入选全国古籍出版社(2023年度)百佳图书、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时代好书”,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广泛好评。
《系年校笺》旨在对《唐大诏令集》进行全面校勘、系年、笺注与辑佚,为研究者提供接近原貌、翔实准确的基本文献。《系年校笺》考据完备,体例精详,是一部集学术性、资料性、可读性于一体的鸿篇巨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其学术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校勘上,以中华书局2008年版为底本,以广东省图书馆所藏明抄本、原北平市图书馆所藏之甲库本、《适园丛书》本、《四库全书》本、《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唐文萃》《资治通鉴》、各唐人别集、《全唐文》所载录之唐诏令为对校本,以学林本为参校本,进行全面校勘整理,通过认真比较、斟酌、讨论,使文本更加准确完善。在校勘中,除利用传世文献外,充分吸纳出土文献成果,如唐代石刻、唐人墓志等。
其次,在作者和作年考订上,原诏令多有未注明作者或颁布时间者,不利于研究其诏令颁布的历史背景和必要性。著者借助各种历史文献,考辨诏令作者,考索诏书颁布时间,考证诏令载于某典籍,从而实现对《唐大诏令集》重新系年的目的。
再次,在字句笺注上,涉及的主要历史人物和重要的历史事件,都给予较为详细的介绍,便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诏书颁布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对关键而难解的词语、名物、典故、典章制度等进行阐释笺证,便于读者和研究者理解诏令的意义。
第四,文献辑佚之力甚大,之功甚伟。由于现存《唐大诏令集》各版本都佚失相同的23卷,《系年校笺》考索比勘有关典籍文献资料,辑佚补逸成一卷,分为上篇、中篇、下篇,共计64篇,并加以系年笺注,附于该书之末。这些辑佚出来的诏令,虽然并非所佚失之全部,但数量亦可观,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可谓竭泽而渔,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唐大诏令集》现有版本残缺的遗憾,其功莫大焉。
《系年校笺》虽然出自多人之手,是团队整理研究的成果。但在体例上严格按照统一标准,在笺注行文风格上保持基本一致。既强调注释的准确性,也重视表达的通俗性,语言洗练老道,表述简洁准确,显示出扎实的语言功力。体现出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有机统一,为古雅深奥之诏令文在当今社会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唐大诏令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法学、科举学、民族学、文学等思想智慧、审美情趣和价值理念。《系年校笺》的出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权威可靠的唐代诏令研究资料,更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人文学科研究需要跨学科融通,对《唐大诏令集》的研究,将更加需要历史学、文献学、政治学、法学与文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无论是哪个专业,阅读《系年校笺》,回到唐代历史现场,可以让读者深入历史的褶皱,聆听大唐最高层的声音。
日本作家、评论家武田泰淳在谈及中国文学的政治性时说:“不是政治家的文学者,不适宜接近世界的中心,也不被垂名于青史。”这番话也提醒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走近诏令,就是接近世界的中心。刘勰《文心雕龙·诏策篇》赞语曰:“辉音峻举,鸿风远蹈。”诏令,作为朝廷昭告臣僚与天下的文辞,光辉的声音高高扬起,宏大的风声向远处传播。我们也希望,《系年校笺》以其学术品格,能名声远播,嘉惠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