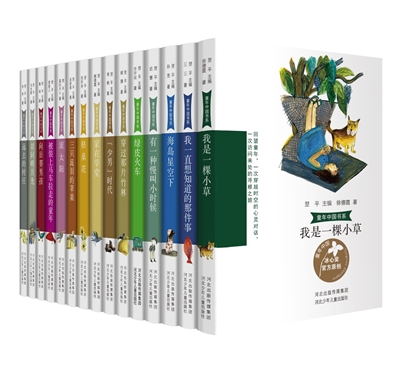■翦悦
冰心先生有句很有名的诗:“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这句诗的一般解读,是委婉揶揄那些孤芳自赏的人,说他们太过高傲,但它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当一个个体,集中关注自身生命体验的时候,自己就变“大”了,大到充满整个世界,那天地呢,自然就变“小”了。
所以如果问我“‘中国式童年’如何‘大写’”,我的回答可能是:从“小”开始。
我所指的“小”,首先是“关注个体”。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关注个体的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参差多态。其实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宏大叙事——大主题、大背景、大文化、大数据,但这些宏大叙事的背后,可能一个个微小的个体,会被压缩;他们的声音,会变得模糊。在伦理学上经常会有一种难题:遇到危险,你是愿意牺牲一个人,还是牺牲10个人?作为理性动物,我们可能会做数学题——牺牲掉人数少的,或者社会价值更低的;但作为感性动物来说,这个问题和数学没关系,如果你是在场的一员,那对于你来说,你就是世界——所以我们才会对那些自我牺牲者报以崇高的敬意,因为对他来说,他牺牲的不是自己,而是整个世界。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我的认识里,关注个体,是我们作为感性动物的重要价值,也是作为写作者的重要价值。我理解的“大写”,其实是把一个人“放大”的过程,去塑造一个(或者是一群)饱满丰富的“个体”,把他(或他们)呈现给同样饱满丰富的读者。在其中,可能蕴含着一些我们渴望传递或寄托的东西,也或许只是一种表达和分享。
塑造个体,真实是必要的。我小的时候不太分得清真、善、美的差别,长大之后,才慢慢了解。很多时候,真不完全是善的,也不完全是美的,但它真。真就有打动人的力量。当然,面对孩子,我们有义务做一些调整,但它的底色一定是真实的。真实离不开生活,也离不开细节。对于个体来说,真实往往意味着差异化。
这又回到刚才说的“大”这个问题上了。最近一个很火的社会话题是人工智能ChatGPT,它是建立在庞大数据和语料模型基础上的。此次讨论会的主题,我也问了ChatGPT。ChatGPT用不到3分钟的时间给我出了一份演讲稿,我看了一下,写得很范式。它上来解读什么是“中国式童年”。原话是:“这并不仅仅是指在中国这个国家度过的童年经历,更是指许多人共同经历的、具有特定文化背景和特色的童年。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成长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写得很标准,很理性。然后它分条阐述:第一,中国式童年“强调了家庭中的重视”,也就是“家庭”对孩子的影响;第二,“注重传统文化的熏陶”;第三,“应试教育对快乐、健康童年所引发的挑战”。有正有反,有古有今,写得还是有模有样的。当然,它可能不太理解“大写”这个词的语境含义,后面就跑到教育话题上去了。但面对这样的一个工具,或者说这样一个对象,我们作为人类,其实是备感压力的。有些行业或者有些工作,在未来,面对人工智能这样绝对理性的代表时,会坚持不住,败下阵来——就像机器取代人工那样。但我们同时也发现,有些人工其实是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或者说,人可以找到机器难以取代的价值——可能不是技术上的价值,而是情感上的、思考上的或创意上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我坚信面对人工智能,作家这个职业或者写作这门手艺,会坚守到最后。其实也不能说是坚守,新的时代环境赋予了写作新的挑战和需要,但写作自身是有这个潜质的。不过,只有那些关注情感、关注真实、关注个体,能够创作出大数据无法算出的作品的作者,才有可能坚持到最后,成为“无可替代”的一分子。
我对“中国式童年”的理解也很简单,两个维度——空间的和时间的,或者说是地理的和历史的。
“中国”这个称呼,原本就和地理有关。四方正心谓之中,以戈守土谓之国。记得有位先生说过:“中国之‘大’,首先是地理上的‘大’。”这话不假。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我们正因为幅员辽阔,环境多样,这才出现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才孕育了“56个民族56枝花”,这才形成了我们中国人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质。而地理上的“大”,反映在书写上,就是乡土性的参差多态。以“童年中国”这套书为例,你能看到内蒙古草原骁勇的牧犬,能看到西南山区静谧的月光,能看到胶东半岛的豆面灯,能看到祁连山下的格桑花。这些都是空间上的“中国”。
那么时间上的呢?我们自古而来的文化传承、生活习惯、集体无意识,当然还有那些很具象的、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其实对今天这些成熟的书写者们来说,有一个在时间上不可复制的优势。他们生活的时段,恰好处在中国乃至世界从静向动的一个时段。这是一个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时段。在他们小时候,时间还过得很慢,乡村之间还各有风貌,乡党邻里还各怀古风,没有那么“向城市看齐”;而城市呢,我小的时候听过两句歌词:“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这一点北京的前辈们更有发言权。邻居之间、同学之间、大院之间,有今天的北京孩子们不可想象的样子(如果机缘巧合还能跟大象作邻居)。不只是北京,上海、广州……今天的这些大城市,科技、建筑、文化、艺术……现代文明层层包裹、堆叠起来的城市。有些部分是变得越来越好了,但同时大家好像做了整容手术,各自的面相变得趋同起来,个体的生活模式好像也都差不多。其实这也影响到了孩子们和他们的童年。城市面貌和生活的趋同、价值观的趋同,很容易让他们的童年也变得趋同。即便是多元化,很多也是在有限空间内面向未来(甚至说更加西化)的多元化。但就像飞蓬一样,即使飞到高处,飞向广阔天空,却很难找到自己的根,找到自己原本的所在。
流沙河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东方式思维中一些持中的部分,内敛的、温和的、静观的部分,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科技化乃至西方化的世界语境中看,某些意义上可能更加符合“人文”的本质。而这种东方式思维,就藏在“中国”漫长而广阔的时空里,藏在乡土中国的记忆里,藏在各位写作者笔下的世界里。可能在写作中,我们要不断思考和探索的是,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的孩子们,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能带给他们的又是什么。让他们以什么样的面貌和自信去面向世界,去拥抱未来;又如何引导他们用自身的触感了解世界,而非用世界的概念界定自我。大写中国童年,终极目的并不是创造一个个“大写的故事”,而是塑造一代代“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