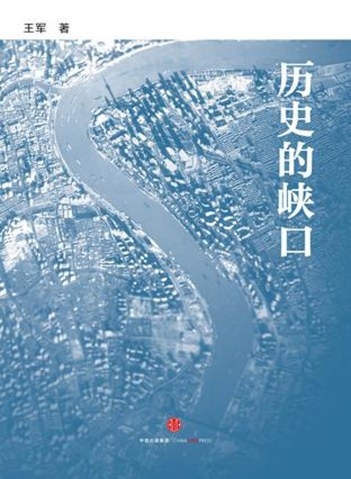关键词 社会转型 城市规划
■受访人:王 军(作家)
□采访人:吉永财(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首都计划”的教训
□“历史的峡口”这一书名有何深层含义?您想在其中探讨什么问题?
■人类社会的转型,说到底是公私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转型和公权力治理模式的转型,城市规划也是在这个层面进行的。公共服务带来巨大的社会增值怎么分配?财政模式应该是什么样?这是这本书想集中探讨的问题。
之所以叫《历史的峡口》,是我觉得,中国社会历经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转型,现在已经冲到峡口上了。现在土地税制改革已经在推进中,这场改革对中国社会公私关系的调整意味着什么?这本书也想探讨。
□在您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城市规划都有哪些缺憾?
■比如1929年的“首都计划”,因是否在南京老城之外建一个新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希望在老城内的明故宫建中央政治区。支持方是中山陵的设计师吕元直,国民政府的德国城市规划顾问。反对方是孙科领衔的“首都计划”班底。班底里的美国顾问茂飞在做“首都计划”的过程中,一直在考虑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继承创新。不过此计划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且没有执行。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蒋介石“居中而治”的想法。
茂飞的规划实际上是要顺着中山大道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带状体系。吕元直的方案则是“中正之位”,变成一个单中心的结构。这样规划一个几万、十几万人口的小县城没问题,但要规划一个百万、千万人口的城市,这个结构太脆弱了。以至于后来的北京、莫斯科、首尔、东京都因城市是单中心——就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区,郊区都是睡城,出了问题。
“梁陈方案”不敌苏联模式
□著名的城市规划方案“梁陈方案”,在1949年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它主要面临什么阻力?
■ “梁陈方案”的精髓就是要促进城市的平衡发展:每个区域要平衡,不把就业集中在一个点上。这个方案跟茂飞的规划相似。“梁陈方案”和“首都计划”都是在一个国都刚刚设立、面临大发展时提出的,那时是完善、调整城市结构的一个最有利的时机。
□但北京后来还是采用了“苏联模式”,为什么?
■1930年莫斯科做了一个规划,其中也有另辟新城的方案,但遭到了斯大林的反对。后来苏联专家来指导北京做规划建设,毫无疑问是不能赞成另辟新城的。他们跟梁思成产生了对立。决策层出于什么想法采纳苏联专家的方案,还需要更多的档案来支持。
□就目前首都城市规划的实际发展情况看,当年“苏联模式”遗留的弊端是什么?
■莫斯科堵得一塌糊涂。两年前,莫斯科公布了一个新方案:把莫斯科往西南方向扩容,在新扩的地方建设一个中央行政区。这个方案把一些部委搬过去,但把总统府留在老城,这是很明智的——如果把中央政府全搬走,老城区的不动产价值一下全缩水了,要出严重问题。
搬迁解决大城市病
□吴良镛后来做了一个“京津冀发展规划”。它总体上可以被称作多中心的方案?
■我所理解的老北京和新北京是共存的关系。老北京被毁掉,新北京也会出严重的问题。在老城上建新城,建出来的城市一定是单中心的脆弱结构。吴良镛从1979年就开始为此而努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走出同心圆”。他后来做了好几期“京津冀的区域规划”,想改变城市功能过度聚焦于北京市的中心、过度聚焦于北京市的问题,想面向更为广大的领域对其进行有机疏散。
我相信他的这个想法对决策层产生了很大的触动。现在京津冀一体化等战略性规划的纲要都已经在做。
□现在很多人在谈首都的一部分政府部门是否应搬迁、如何在通州建行政副中心的话题,您怎么看?
■我在2004年的报道《中央行政区迁移悬念》中集中介绍了赵燕菁——当时中国规划院的副总规划师。赵燕菁认为,要带动北京城市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要带动中央行政区域的优化和调整。他把首都的行政功能和北京市的功能在空间上进行水平分割,因为全国各地的人来北京办事,主要是找中央政府办事。他的基本观点是,应该把中央行政区设在通州,让中央的一些部委集中在那里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