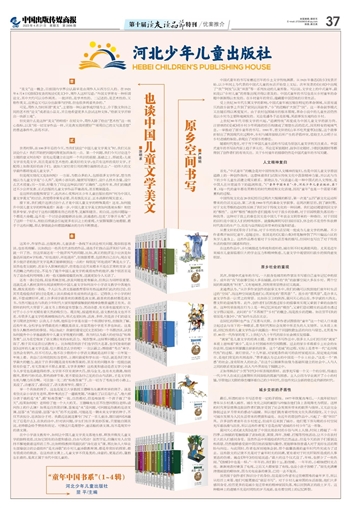■严晓驰
中国式童年的书写有着近百年的乡土文学传统渊源。从1921年鲁迅《故乡》发表开始,以少年闰土为代表的中国式儿童的生活开始登上文坛。次年发表的《社戏》中出现了“我”“阿发”以及“双喜”等一系列生动的儿童形象。可以说,文学史上的中式童年,最初是以“乡村儿童”的形象出现并得以普及的。中国式童年的书写也是从乡村童年的命题中渐渐得以生发的。在乡村童年的背后,蕴藏着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受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影响,中国式童年被压缩在特定的革命领域,从原有逼仄的故乡叙事上升到了家国认同叙事,“乡”的范畴扩大到了“国”。这一革命叙事模式又在随后得以再度复兴。由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根本展现,革命小说中的儿童生活仍然是以乡村为主要阵地阐发的。无论是潘冬子还是张嘎,其故事发生地均在乡村。
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追溯传统”再度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新方向。汪曾祺的《受戒》将乡村少年明海的经历构建成了理想生活的范式,因其特有的地域气息,一举推动了原乡童年的书写。1991年,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出版,这个故事折射出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乡村与城市接轨后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借助主人公明子从乡村进城的体验,表现出了对原乡的眷恋。
随着时代变化,对于当下中国儿童生活的书写成为原创儿童文学的关注重点。中国式童年的书写在内容上趋于多元化。不论是军旅题材、战争历史题材、少数民族题材等都得到了创作者们的有效关注。关于乡村童年的描摹仍然是中国式童年的书写关键。
人文精神复归
首先,“中式童年”的概念是对中国传统和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原创道路上的一种创作指向。这意味着我们试图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并以此与当下的少年儿童生活建立现实联系。郭艳认为,“汉语童心是一种中国式的人文传统,是中国人在日常滋养下的温润和美。”(“童年中国书系”·序,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第7页。)每一代的童年都有其特有的时代特质和文化语境,因而“童年”也是一个需要不断重构的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断层,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白话文运动,第二次是1960年代的革命文学叙事。在两次断层后,到了新时期,对于文化寻根的迫切性反映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回溯。我们迫切渴望找回文学的“根性”。这种“根性”被创作者们提炼为对于故乡的依赖,对于田园牧歌失落后的一种找寻。这种对于故土的眷恋其实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带来的一种烙印。对于田园的回归是中国文人们的特殊情怀。就像陶渊明写《归园田居》,怀念的不是劳作和农耕时代落后的生产力,而是与自然贴近所带来的安逸和舒适。
从曹文轩的《草房子》开始,对于乡村的生活呈现一度成为儿童文学的热潮。不少作者都开始回忆童年,追随过往。张国龙的《瓦屋山桑》将笔触伸到了四川偏远山区的失学儿童身上。这些作品都有着对于乡间生活苦难的描写,但同时也写出了对于传统生活的强烈归属感和向往。
在这些作品中,乡村被描述为单纯和质朴的,城市则不时充满着风险。尤其是近年来城市儿童面临着巨大的学业压力和精神焦虑,儿童文学中渴望回归故乡的倾向愈发明显。
原乡社会的重现
其次,伴随中式童年的书写,一大批身处城市的作家在书写着自己童年记忆中的原乡。成年的“我”的叙事空间大多在城镇,幼年的“我”的叙事空间大多在乡村。两个空间的距离既有“时差”,又有地域差,因而常常显得亲切又疏离。
龙迪勇认为,“从许多作家创作的叙事文本中,我们的确可以找到他们童年时生活过的‘空间’,而这种空间就是他们心灵深处的‘原风景’ ”。故乡的“原风景”,是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一以贯之的背景。比如孙卫卫的陕西,莫问天心的山东,李学斌的大西北,曹文轩的盐城等等。此外,创作者们试图透过原乡的描摹来实现父辈到子辈的血脉传承。这种传承体现在行为上是一种记忆深处的“模仿”,父辈们恳切踏实的品质也透过文字得以延续。此时的“乡”不再囿于“乡村”的概念,而是故乡的范畴。如在翌平《我的邻居是大象》中,“我”始终生活在北京。
在回忆的同时也产生了反思与关照。许多作者试图借助“童年”这一个切入口来建立起过去与当下的一种联系,思考时代和社会发展中所丢失的人文情怀。从本质上来说,回忆性质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流露出一种对于田园牧歌生活的向往与留恋,尤其是70后、80后一代作家的笔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原乡社会被反复描摹。
“离家”是儿童文学的经典主题。在童年书写作品中,很多主人公们经历的“离家”本质上意味着“离乡”,是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腾挪。过去的家乡承载着乡土社会的生存法则,但城市则暴露出崭新的故事。这个“进城”的过程,实际上是青年一代“走向现代性”的过程。黄灯曾说,“十几年前,对家庭条件尚可的农村家庭而言,坚定地走向城市,是他们常见的共同选择。”费孝通认为过去的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个以姻亲和血缘为基础所建立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人与外界却处于隔膜之中。
正如苇枫在《“少男”时代》中所表现的那样。故事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分别,传递出一代少年人在成长过渡期所共同面临的孤寂与困惑。主人公因为学业离开了小小的村镇,尽管他以无限的眷恋缅怀着自己的少年时代,但也终究以全新的姿态走向新的时代。
城乡交织的矛盾性
最后,所谓的原乡书写还带有一定的矛盾性。1977年恢复高考后,一大批年轻知识青年从乡村涌入城市。城乡文化之间的割裂与冲撞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得这批创作者们既享受到了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眼界与情怀,又无法完全挣脱过去岁月带来的感动与温暖。所以他们既有着对传统文化失落的隐忧,又十分认可城市发展为人民生活带来的便捷和益处。在近年的原创作品中,兴起了一股“怀旧”风。许多创作者童年在乡村度过,但成年后来到了城市。他们笔下所勾勒的乡村空间充斥着浪漫与沮丧,所以这些作者笔下总是出现“进城的乡村少年”这一形象。
莫问天心的《滚太阳》还原了中国北部农村的乡俗与风土人情,时间上跨越了一年四季,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诸如收麦、蒸馍、拜年、放蜡、打囤等传统活动,让不少在农村长大的人们感同身受。虽然作品中所描绘的时代已然远去,但是今天的孩子们看到这些场景,仍然能够感受到中国百姓的坚韧与勤劳,更能够体悟普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与此同时,作者也深刻地体会到,那个温馨浪漫的童年时代终究成为了过去。这些散文的记录不光是对于童年时光的回溯,更有着对于时光阡陌所造成的人事更迭的伤感。她在《拜年》的结尾说道:“最大的这个仪式没了,年味,也便少了一些热闹。”《放蜡》中也是一样:“一年年的,我们盼十五,盼放蜡。一年年的,小蜡烛把时光点亮。渐渐地农村普及了电视,之后又大都安装了有线,也没小孩子放蜡了。”原先充满着诗情画意的蜡烛夜,因为光电设备的普及,已经一去不复返。
虽然囿于创作者们知识分子的身份,但是部分作者有过贫瘠困难的童年岁月,所以从经历上来看,他们可能更接近“底层书写”。对于乡村儿童穷困的生活面貌,他们大多感同身受,经历更多的是城乡变迁带来的精神家园失落,难以回到真正的故土岁月。这种精神上的遗憾不光是时间性的岁月流逝,也有着空间上的记忆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