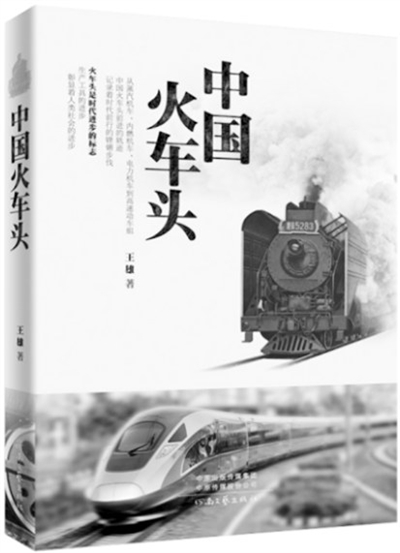○孙晓璟
问问老一辈在铁路上工作过的人,大多听过这样一句话,“离地三尺三,赛过活神仙”。姥姥家住在火车站旁边,小时候一有时间就跑到铁轨上数木枕,木枕与碎石铺就的铁路,遥遥的,一眼望不到边。
后来上了大学,第一次坐火车。那时我们县城的火车站已经是封闭式的了,一排铁栅栏象征性地把站台与候车厅隔开,栅栏的门用一条粗链子挂着。有火车进站时,栅栏门前工作人员就把锁头打开,绿绿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车厢,轰隆隆地开了过来。仿佛是即将进入大学的新奇和兴奋,赋予了这辆火车特殊的意义,从此,我喜欢上了火车。
毕业后从事了编辑工作,有幸接触到一本跟火车有关的图书,顿觉亲切。作者是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主席王雄,2017年我们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见过一面,商量另一本书《中国高铁》的出版事宜。
5年的火车司炉工作开启了他人生的序章,讲起那段经历,王雄老师如数家珍:那时的火车还是烧煤的,想成为一名司机,先要在烟熏火燎的司机室当上一段时间的司炉,而为了探身瞭望方便,司机室两边的瞭望窗玻璃是不能关闭的。冬天,两边的风呼呼往司机室灌,寒气刺骨。夏日里,伴随着一座大炉子,驾驶室又闷又热,衣服沾了汗水和皮肤粘在一起。一个班次下来,至少要投五六吨煤。每次下班,人都累得像要虚脱。而他仅仅用了一个月就熟练地掌握了投煤技巧,并独立上岗作业了。听王老师说,“那时候的火车司机是‘处级待遇’,给个县长都不换”。说这话的时候,他眼中仿佛有一辆吞云吐雾呼啸着的蒸汽机车,正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那是属于他的蒸汽机车,他的永恒记忆……
2018年中下旬,王雄老师将精心写就的稿件交付给了我。我手捧稿件,一方面有着涉猎一个崭新领域的新奇和忐忑,另一方面也有把控如此专业严谨内容的不自信。但当我开始编辑稿件时,发现一切的顾虑都烟消云散,王雄老师还是西南交通大学兼职教授,这样的职业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其创作兼具准确性和文学性,书中的材料大都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采访,对于我的每一个疑问,作者都不厌其烦地悉心指导,至于一些书中插图授权的不情之请,王雄老师也都大方应允。有了这样一位配合度极高的作者加持,《中国火车头》超预期地完成了出版流程,于2018年12月正式面世。
一本书的出版过程,既是编辑工作的过程,也是编辑学习的过程。审稿期间,随着对火车头发展历程的了解,我仿佛懂得了作者对于火车的那份挚爱——
旧中国有着“万国机车”博物馆之称,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为掠夺中国财富,在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强行输入了铁路。旧中国的铁路线上,行驶着200多种型号的外国机车,书写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悲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以研制国产蒸汽机车为突破口,很快实现了蒸汽机车的国产化,满足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958年“大跃进”浪潮,开启了国产内燃机车研制的新征程,而内燃机车中又属“东风型”机车最引人注目。
这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小故事,1957年,毛泽东在《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式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正是由于这句名言,当时最先进的巨龙型内燃机车被命名为“东风型”。
电力机车的发展也在同步进行。20世纪50年代,原铁道部依据国情和铁路装备实际情况,确定了“内燃、电力并举,内燃为主”的方针,因此在1958~1967年10年间,我国总共研制生产了5台电力机车。随着技术难题的突破,我国在随后几十年间,不断尝试完善和优化,加上电力机车启动加速快、爬坡能力强、工作不受严寒影响等优点,在运输繁忙的铁路干线和隧道多、坡度陡的山区线路上更能发挥优越性,越来越适应我国运输工作的需要。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铁路也在快速发展,日本开通的新干线系统,是世界铁路史上第一个时速200千米的高速铁路系统。面对这样的挑战,在“引进、吸收、消化、创新”的战略引导下,原中国铁道部和各大科研机构通过与世界高铁强国合作,实现动车组技术跨越式发展,研制出具有中外联合生产特色的和谐号CRH系列高速动车组,运营速度达200~350千米/时,运行于中国国内一大批新建高速铁路。
时至今日,时速300~350千米/时的高铁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的出行方式,甚至在济南至郑州高铁线的濮阳至郑州段成功实现明线上单列时速435千米、相对交会时速达870千米,创造了高铁动车组列车明线和隧道交会速度世界纪录。
飞速发展的新中国铁路,让世界刮目相看,从技术最先进的前进型蒸汽机车、到牵引量最大的和谐型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再到速度最快的复兴号高速动车组。而《中国火车头》正是一部记载着中国100多年火车头发展历程的作品。正如王雄老师在引言中所写的那样,火车头是时代进步的标志,生产工具的进步彰显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火车头》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单元;《中国火车头》的每一组音符,都是中国铁路交响曲的雄浑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