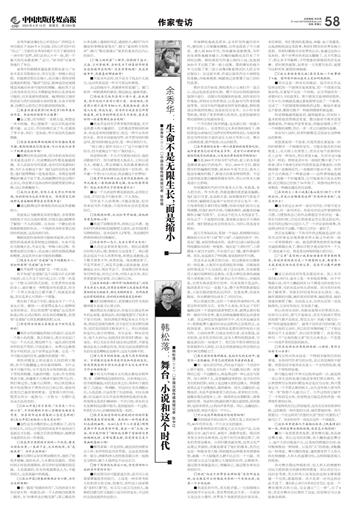■余秀华(诗人)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佳璇
余秀华新诗集《后山开花》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4年4月出版。《后山开花》中的“后山”二字取自余秀华《或许不关于爱情的》一诗中的“走吧,我们去后山大干一场,把一个春天的花朵都羞掉。” 近日,“好书探”对余秀华进行了专访。
余秀华的眼睛里蔓延着无限生命力。“生命不是在无限地生长,其实它是一种缩小的过程。你能察觉到它在缩小,而且缩小到你觉得还满意的程度。”她语气坚定,眼神也坚定地缓缓道来她对生命可能性的理解。她坦然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并认为舞蹈延伸的应是身体的可能性,而非美感和柔韧度。她用轻松又俏皮的话语与我们诉说着生命的厚重,生命不再厚重,仿佛后山的花已然在眼前悄然绽放。
□恭喜你最近获得《时尚芭莎》的年度女性作家。参会的时候有什么趣事?
■去之前,因为韩红一直做公益,我想送一本书给她。我心想她不一定认识我或对我感兴趣。去之后,不仅给韩红送了书,还遇到了李宇春,我们一见如故,李宇春说我是她的偶像。
□你在英国跳舞的视频实际传播效果很不错,看到视频我们很感动,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跳舞这段经历吗?
■跳舞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本来就是这样子,完成舞蹈动作都是勉勉强强。有人说没有任何美感,没有任何美感的时候,为什么来做这个事?他们这样说我也不愿想,他们觉得舞蹈一定是要美的。我现在觉得舞蹈的重点不在于美,而是跳舞时你会出现什么反应,你在展示这些动作时到底需要怎样去做,这让我感触很大。
□我们注意到,实际上在文学之外的领域,你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变大。你觉得自己的视野或者接触的事情在变得更丰富?
■通过跳舞这件事情给我的启发和感触很大。
我原来以为跳舞是非常优雅的、非常柔软的肢体才可以完成的事情,但现在通过跳舞我了解到一个人的局限。比如说一个健全的身体能够做到的生活,一个残疾的身体非要达到同样的高度,这是我的目的。
舞蹈是把你身体的可能性再延伸,而不是把你的美或者是柔韧度达到极致。生命不是在无限地生长,其实它是一种缩小的过程。你能察觉到它在缩小,而且缩小到你觉得还满意的程度,这是我对生命可能性的理解。
□现在大众对“恋爱脑”这个词褒贬不一,你如何看待“恋爱脑”这个词?
■我不觉得“恋爱脑”是一个贬义词。
我不知道“恋爱脑”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兴起的,近几年这个词兴起之后,它第一次是以一个贬义词的形式出现。它更多用在女性的身上,就好像有一种贬低女性的意思,你为了一个男人你连自己都不做了,你就是恋爱脑,其实是多么可贵的一个现象。
现在到了我这个年纪,谁还会为了一个人舍生忘死。爱情——我觉得这是人心里特别宝贵的存在。所以我觉得“恋爱脑”这虽然开始是以贬义词出现的,但在我的理解里,我觉得“恋爱脑”应该是被褒奖的贬义词。
□你觉得女性独立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怎样的?
■现在女性的崛起和独立的意识,还处在一个微小的范围。真正的独立,真正决定自己可以一个人生活,哪怕两个人一起生活时觉得我和你是平等的,目前还很少。如果完全做到男女平权的话,这个世界也会失衡。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我的爱情一样。
两性问题是上帝设置在人间的两大障碍,你不可能翻越上帝设置的障碍。为什么说不可能平权,它不是因为女性的软弱,而在于男性的粗糙、力量的问题。比如,作为男性我说不赢、讲道理不占理讲不赢时我可以打,我打得过你,力量可以取胜。所以我觉得女性平权还取决于男性对自己的认知,他如何改变自己基因里的野蛮。这有很大的空间,要男女双方一起努力,一方努力一方摆烂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后山开花》序言里写:“文字是一个人的心态”,不同时期的不同心态都会反映在文字里。你在创作这本诗集时心态是怎样的?在《后山开花》出版后心态又是如何?
■创作这本诗集时的心态我都忘了,因为时间太久。《后山开花》里的诗是多年前的诗只是新近才出版。出版之后我觉得挺好,能够读书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你在序言里提到目前的一个状态:像是头埋在水里,一直游下去,无目的地写,与“荒诞共存”。为什么这样说?
■我写序时正好在看加缪的书,他给了我很多感触,他的生活、人生都是荒诞的。那段时间正好是疫情期间,我写序时觉得真的很荒诞。人是荒诞的,所有的荒诞都是人为,不能怪别人,这是荒诞中的荒诞。
□《后山开花》诗集的架构分为六辑,为什么这样架构?
■第一辑是“纸做的村庄”,写我的家乡和我在家乡的一些感受;给一个人的情诗收集第二辑里,为“如果我也在桃花源”;第三辑是我许多在路上遇到的风景,遇到的人;辑四“向不确定的事物索要亮光”、辑五“意如明月知秋深”、辑六“梨花落满头”更多的是我自己内心的独白。
□“路上的风景”一辑中,你提到了海口、上海、兰州等城市,当时是为了诗集创作特意去这些城市采风吗?还是另有他因?在这些城市中,你最喜欢哪座城市?
■不是采风去的,我不会为了钱去什么地方,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去过的城市中,我最喜欢的是厦门。厦门给我一种很清爽的感觉,靠近海边,植被茂密。
□你说自己依然在写小情小爱,在我看来,你不仅仅只在写小情小爱。恰恰相反,你是将小情小爱作为切入口,更能感知爱、进而进入大爱、传达大爱。你为什么说在自己所有的爱里,对文字的钟情是经久不衰的,甚至是任何一段爱情都无法企及的?
■我也不是对文字有多强烈的爱意,文字是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它好像没有特别的神圣,我也没有特别需要它,而是一种天生共存的关系。我并非刻意地写作,在不想写的时候会写,想写的时候也会写,是一种日常的行为。
“将小情小爱作为切入口”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因为爱情这个“切口”最好进入。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写爱情诗的话,他的诗歌就不行。因为爱情是人体会人、之所以成为人、理解人,再去理解人类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句话,没有爱情的话没有一切东西。你不爱一个男(女)人的话,你会爱这个世界吗?
□很多作家和诗人认为写作是孤独的、创作之路是一条荆棘满布之路,你如何看待写作?你认为写作之于你意味着什么?
■每一个人的创作都是孤独的,必须独立完成,不可以也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参加。
写作是个人的事情,可能会孤独,但对我来说写作不孤独,只是你的生活状态孤独而已。
□你提到加缪,从2020年开始读,读他的书有怎样的心得?
■我读了加缪很多书,具体已记不清。他的《西西弗的神话》能够把人读死,还有《鼠疫》写得特别好。还有《局外人》等等。我觉得《西西弗的神话》写得最好。
□你在创作心态上、生活上有什么变化?
■人肯定会有很多变化的。相比以前想讨好别人的心理,我现在完全没有了。我以前还会说这个诗人我喜欢他,我想去请教他;这个歌手很有才华,我喜欢他。现在都没有了,不是不喜欢了,而是不会像之前故意地、很执拗地去交往,现在不会了。我觉得讨好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对自己无效,对别人也无效,所以我更愿意宅在家里,自己跟自己玩。
□这本书的第一辑叫作“纸做的村庄”,对很多文学名人来说,经常会在精神上或直接在作品里回到自己的故乡,称之为精神原乡。你作品里也经常写到村庄,你对村庄的情感是怎样的?
■他们说精神原乡,我想横店村作为我的精神原乡也是可以成立的。
横店现在有点像景点,但是它以前在我40年的生命里,是存在的,我的随笔里写了很多关于家乡的诗。我的诗现在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你说它是现代情诗,它不是它又有田野包围你,说它是田园诗又根本谈不上。所以我面临的是内心故乡的情结。其实这是一种生活变化,每个人的内心包括我们的邻居们都会一起变化。所以无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都会改变,你是无法说清楚你丢失的究竟是糟粕还是精华,这说不清辨不明。
□有人写乡村的衰败,也有人写乡村的振兴。乡村最近这些年存在外在和内在的变化,你觉得现在的乡村文化在整个文化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现在都处在转型期,有一段断档或空虚的时间。比如有些山区,因为地势偏远,村民走出来之后,很多村子就荒废了,它就是一种凋敝。但是村庄文化凋敝以后,人还活着,只是改变了生活环境。村庄在凋敝,但是城市文化并没有得到相匹配的发展。我觉得这是我们精神的一个空白档,所有的文化发展和沉淀都不稳当,是很摇晃的一个过程,和我们人内心的精神摇晃是一起的。
□很多采访过你的记者提到对你的印象是聪明甚至有些狡黠。在你的一些作品里我们也读到幽默。比如《五月十二日清晨》明明是两个年长的男性吵架,最后一句“大伯,加油,你不能吵输了”顿时就消解了前面诗句里的硝烟也好、日常喧嚣也好,你觉得自己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吗?
■廖伟棠第一次见到我,就说我的诗歌有点小坏,有坏坏的东西在里面。这也是我性格的一部分,诗歌和诗人的性格是联合在一起相互交映的,换个人他肯定不会这么写。
□除了写诗你也写过小说,你觉得诗和小说的写作有何不同?
■我觉得写诗可能更适合我,因为写小说需要掌握更多的技巧。小说是一种非常考验人性和语言的文体,很难写,我听说小说家都是“老奸巨猾”的。有又写小说又写诗的人,能够把诗歌写好又能把小说写好的也有,不过同时达到高度的肯定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