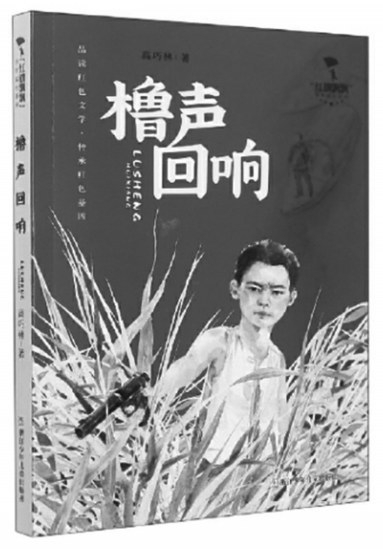○王忆莎
什么样的作品对于少年儿童来说更有吸引力?我想,高巧林创作的《橹声回响》这种兼具可读性与艺术性、充满魅力的作品应是一类。《橹声回响》的魅力,一方面源于小说在众多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找到了独特的抗战童年书写角度,拓展了抗战题材儿童小说的叙事空间与文本思想性;另一方面则在于小说中“童年精神”所带来的别样审美体验与生命经验。
作者高巧林以童心塑造了“非英雄化”的战争题材儿童主人公泥蛙,形象生动而立体,避免落入“小英雄模式”的窠臼。小说更是将宏大的民族战争叙事还原到日常生活与人际交流之中,从儿童的感性历史来呈现正史中那些被忽略的小人物的生命经验与丰富感情,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相辅相成,引人入胜。
当然,儿童视角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儿童对于世界的认知主要仰赖于个人的感性体验,缺乏宏观把握世界的能力。当以儿童视角来讲故事时,成人叙事中可能出现的情节硬度和张力则会被舍弃。但《橹声回响》通过“对话”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橹声回响》虽然选择了小切口的写作策略,从泥蛙的儿童视角来铺写文本,但那些未曾进入泥蛙视野的历史和时代却没有被完全遮蔽。小说写的是1939年秋发生在苏南水乡的抗战故事,但涉及的人事却不限于此。作者通过泥蛙与成人形象的对话,将“三年前日军轰炸苏州城”“吴大顺赴日经商”等事件纳入文本之中,代际视野的良性互动扩大了文本的叙事张力,使儿童的生活点滴与历史时代的浮沉互证,在泥蛙的儿童世界里呈现了几代人的伤痕与创伤,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泥蛙的成长也是在代际视野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的。远藤与泥蛙的对话尤为重要。被迫来中国服役的日本军医远藤与孩子泥蛙展开了一场关于家乡、关于儿子的温情对话,使人性之花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温暖绽放。这场对话还引起了泥蛙关于好人坏人的思考。敌方阵营不全是“坏人”。所以一个人究竟是“敌”是“友”,是“好”是“坏”,这是需要泥蛙自己去判断的。
高巧林站在童年的立场上来言说战争,这样处理削弱了成人理性对战争的阐释与评价,使得全书对于战争的书写始终限定在少年儿童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小说的整体风格与语言都并不沉闷,反而透出童真童趣的烂漫与轻快,体现出了儿童文学本身“轻逸”的美学特征。在孩子的世界里,子弹是“长生果”,烂泥是“炸弹”。这样一种“举重若轻”的天真与豁达在美学品质之外,更是一种童年精神的折射,即儿童遭遇沉重磨难之时所显示出来的韧性、勇气以及永不言弃、永不堕于黑暗的坚定信念。
对于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来说,把握“轻”与“重”的度是个难点,过“轻”则消解了题材本身的意义,过“重”则易让儿童读者承受过分的成人悲哀。而《橹声回响》借助游戏使“轻”“重”达到了某种平衡。战争年代的童年是破碎的,对于当时的少年儿童来说,游戏更是负载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战争来势多么汹涌,都不能磨灭儿童内在本能对于快乐生活的渴望。直到最后一章,泥蛙仍在坚持训练水牛打鬼子,用自己最真实的童年生活来对抗重重劫难。
紧接着,作者又呈现了成人的非游戏性的战争空间。在成人的战场上,战争双方都有着大量的死亡。儿童游戏与成人实战的并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当现实世界中成人被欲望所控而落入暴力、倾轧的深渊时,儿童依然可以在生存的夹缝中找到“游戏”这类自由呼吸的出口。或许作者正是借游戏与童年精神对真实的战争发出强烈的批判与谴责。
《橹声回响》是明快舒朗的儿童战争文学,故事情节在走向悲剧时总能“柳暗花明又一村”,有厚度但不过分悲伤,是适合儿童阅读的抗战题材小说。在小说结尾处,泥蛙表达了美好的期望:“如果日本军队里多一些像远藤一样的人,那就好了!”这何尝不是作者借泥蛙的儿童视角来完成对历史的重新思考与感叹。战火无情,民众何辜,最后的祈愿是难以弥补的遗憾,但却提醒着我们珍惜身边平凡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