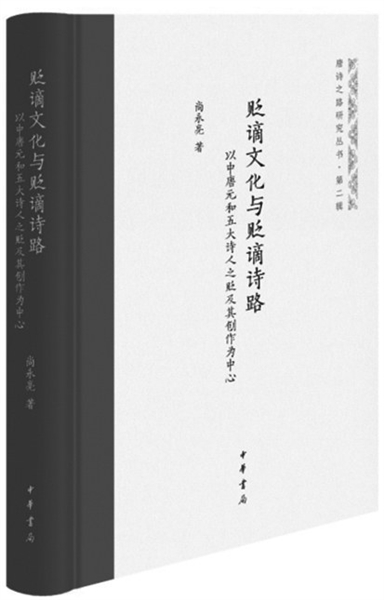关键词 贬谪文学 诗人 生命力
○徐嘉乐
贬谪文学与贬谪文人研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始终是尚永亮先生治学发力所在。自20世纪80年代始,尚先生就展开了对贬谪文学的研究,而后数十年继续在此领域辛勤耕耘,系统地构建起一种研究范式,创作出一批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贬谪文化与贬谪诗路——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是其相关研究的精髓汇聚之作。
该书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近年来撰写且未公开发表的成果,主要聚焦于贬谪诗路研究;另一类则是不同地区刊印过而又有若干改订的代表性成果。这种新旧内容的叠加,既使得经典之论经此次增删后愈发精进,又与时俱进,增添了当下的学术思考并形成完整焕新的研究理路。谭学纯先生曾论断:“无论是研究贬谪文化,还是研究贬谪文学,学术界都无法绕开尚永亮。”(《在大视野中逼近研究对象》,《古籍研究》2005年下卷)可以认为,20年过去,尚先生再次为学林呈上了一部令学界难以绕离的著作。事实上,较诸其学术价值,该书所展现的纯然生命力的观照和解读更值得关注,这种观照、解读又可细分为人文主义关怀、悲剧审美意义与强烈的时代精神价值。
首先是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翻阅该书,读者就能切身地跟随作者,感受其对于贬谪文人们惨痛遭遇的同情与悲悯,对于他们因贬谪而展现出的关乎生命的哲学沉思,有如一把把重锤敲击着读者心灵。日本学者厨川白村认为“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苦闷的象征》),同理,尚著在对资料全面占有的基础上,精准地把握住了“生命的沦陷与挣离”这条主线,令读者清晰地感受到由贬谪生成的这种极具生命力的文学内里,有生存的苦痛,有反抗的呐喊,更有在困境挤压中迸射的光芒。作为中国古代对官吏的一种惩戒手段,贬谪冷酷无情地将“负罪官吏”发放荒僻之地。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贬谪不仅是一场影响人生境遇的政治灾难,更是对其政治理想、品节操守、人格尊严的无情摧残,使他们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忧患与苦难。在这一过程中,文人们得以重新认识、剖析自己,或发出“比琼虽碌碌,于铁尚铮铮”的强音,或发出“红颜与壮志,太息此流年”的呜咽,或发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高唱,其中展示的是一场痛感与快感兼具的生命体验,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欢乐和大悲哀,大真实和大虚幻”。也正是这样的生命体验,常常逼迫着古代文人在困境之中激荡出超越“专制王权”的心灵力量,使得他们在咀嚼苦难的同时,越过平常的尺度,得以从痛苦中超拔出来。尚著通过对中唐韩愈、元稹、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五大诗人的细致考察,提升为哲学意义上的对生命力的讨论,表露着这样的理念:人心对自己的领会,往往是通过与这个世界的失败斗争而实现的,使这些文人伟大的,并非贬谪事件本身,而是在社会政治层面无法实现理想与价值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在无限的孤独中保留自己、肯定自己。
其次,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读者亦可获得艺术上的悲美感受。这种审美性源自作者对古人生命历程及其作品的敏锐洞察与透彻解析。作者对精神分析学与文学心理学的大量运用,令其既能入乎其中,在细密的针脚中体悟贬谪文人的鲜活生命,又能出乎其外,串联起连绵不同的生命个体所组成的文化时空。文学始终是人的学问。它理应是人类情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载体,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映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学始终关注着人类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尚著对于贬谪文人与贬谪文学的研究,就展示了这样一种对人灵魂的研究,更准确地说,是对人的充满纯然生命力的灵魂研究。在阐述贬谪文人之精神与文学格调二者关系时,作者申言:“精神的伟大源于人性的坚强,坚强的人性必定导致与其相应的文学格调。如同只有屹立江中的巨石,才能激起奔腾的浪花,只有傲视风雨的林木,才能发出动地的呼啸,贬谪诗人饱经苦难仍不降心辱志改弦易辙的悲愤长鸣,必定散则万殊、合则为一,形成孤竹焦桐般的激切音响。”书中通过直接抒情、寓言讽刺、理性认知和咏史抒怀四种方式,系统地论述了元和贬谪文人的孤愤情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并进一步指出这些情怀和表现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元和贬谪文学的精魂——悲剧精神。将悲剧精神从繁芜的文学作品中拎出,可谓探本之论。它带给读者的,不仅是生命的启迪,也是贯注着孤愤情怀的抗争精神和悲美体验。
最后必须认识到,该书对贬谪文人与贬谪文学的研究,充满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价值。细读尚著,也许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方案,即从那些贬谪文人身上找寻到重建失落精神的答案。作者认为贬谪文学最富光彩也最耐人品味的文化内涵就是贬谪士人所流露出的两种对抗命运的生命倾向,一是执着意识,一是超越意识。他将这些贬谪文士身上最具亮色的意识和气质揭示出来,给处在当下正遭受“信仰缺失”痛苦的人们以警醒。或者可以说,无论是贬谪文人执着意识中“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命运的挑战、对人的尊严的维护”,还是其超越意识中“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全面反思、对是非荣辱和狭隘小我的淡漠遗忘”,都能在这个时代滋养残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