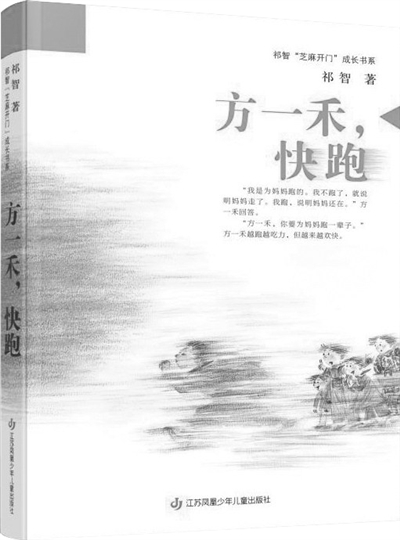○祁 智
30年前的早春,我去北方进行了一次采访。
一个 8 岁的小女孩,暑假里爸爸在她和妈妈面前去世。妈妈患有顽固性类风湿性心脏病, 需要住院治疗,但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医院便帮忙设立了家庭病床。
我见到小女孩,是在半年后,她 9 岁的早春。每天,小女孩做早饭,狂奔去医院拿盐水瓶,然后喂妈妈吃早饭,狂奔着去赶公交车; 傍晚下公交车,狂奔着回家做晚饭……
小女孩独立支撑家庭的情况,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完全清楚。后来,三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叔叔从侧面了解了,就暗地里帮扶她。再后来,学校从一个细节上发现了——班上收费, 同学们交的是整钱,唯独她装了一小塑料袋的零钱。
“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呢?”我问小女孩。
“又不是什么好事,”小女孩笑着说,“每家都有自己的事,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我能干的。”
我采访了那三位叔叔。他们告诉我,尽一点所能,但他们很小心,唯恐伤害到孩子。
“搞不好,帮助也会成为伤害。”一位叔叔说。
学校也是如此,小心翼翼,如同呵护一朵被风吹雨打的小花。
30年来,我的眼前总能看见那个瘦弱的小女孩在奔跑——双臂摆动、双臂垂直、一手压着背上的书包一手划动。但那次采访之后, 我没有主动和小女孩联系过。虽然小女孩总是面带笑容,我写的报道题目就是《微笑着面对生活》,但我拿不准,哪怕是一句话,会不会伤害到她。过早失去爸爸而陷入悲伤的泥沼, 不是说跨就能跨过去的。
我不敢主动联系的另一个原因是怕提起妈妈。我见过她妈妈,脸色苍白、一头乌发。妈妈久病成医,自己能给自己输液。她自知活下去很难,但为了不让女儿成为孤儿,她要拼命活下去。
有一天,女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考上了家乡的大学。我为她高兴,暗暗揣度:她没有离开家乡,一定是为了陪伴妈妈吧?又有一天,女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毕业了,要去南方工作。我为她高兴,但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30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始终没有动笔,就一个原因:不忍心。30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就一个原因:不甘心。30年来,我一直有意识地采访学校、 家庭、孩子。我获得了更多的故事,也在获取动笔的决心。
我请教一位小学校长,如果一个孩子的家庭发生变故,学校知道吗?校长说,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问为什么。校长说,有的家长在第一时间和学校沟通,有的家长会先瞒着学校,以后再说,也有的家长一直不说。
“为什么隐瞒呢?”我问。“总之……不是好事吧,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也不想麻烦大家。”校长说,“其实……你我不也是这样?”
我问:“呃——那孩子在学校怎么办?”“家长主动和我们沟通的,我们会小心,制订方案;我们如果不知道,真没有办法。” 校长说,“有时候‘疏漏’也是关心。”
“那不会伤害到孩子吗?”我问。校长说:“孩子是单纯的,知道你不知道——不知道就没有伤害。”“但学校很快就会知道,”校长又说,“时间一长,什么不知道?”
“知道了怎么办呢?”我有些紧张。“想方设法,和孩子一起‘过来’。” 校长说,“陪伴一段,关注一生。”校长告诉我,其实学校都有预案,但一旦有事,所有的预案都用不上——事情发生在鲜活的个体生命上,必须有“个案”。
伤口愈合,一般分两种:一种,内里与外表同时愈合;还有一种,每天把愈合的表面划破,等内里长好,再一起愈合。后一种很深。无论哪一种,都需要时间。生活总是朝向希望的。我们有幸参与了孩子的一部分人生,后续的便是绵长深情的祝福。于是,我决定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方一禾,快跑》。小说完稿是凌晨2∶30。我打开门,走到户外。春寒料峭,暗香浮动。我恍惚是在30年前,披星戴月,要赶乘北上的绿皮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