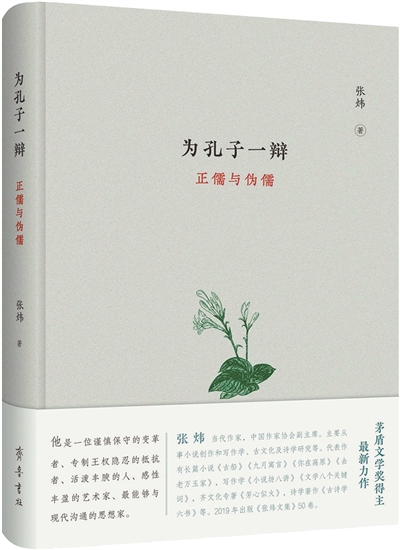关键词 作家 孔子 儒学
○赵月斌
“作家-知识分子”的巅峰文本
如果说写作是一门手艺,作家便是操持文字的细作匠人。只不过有的作家成了文字的炼金术士,有的充其量只是文字的搬运工。张炜显然属于前者。正如萨义德推崇的“作家-知识分子”,张炜不仅是以原创立身的作家,还是敢作枭鸣的知识分子。在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多产而又多面,不仅创作了巨量的小说、散文、诗歌、文论,而且深耕古典,精研传统,跨越文体,打通文史哲,先后创作了《小说坊八讲》、“古诗学六书”这样的诗学专著,以及“徐福研究”、《芳心似火》等续古传今的史论考辨。这种全息式的写作实践,使得张炜的作品呈现出厚重的质感,并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
张炜曾说过:“一个写作者最后要修起一个尖顶,避免化为废墟。随着成熟和苍老,最后挺向苍穹的,不一定是虚构的故事,需要稍稍不同的构筑材料。当然,一个好作家什么材料都有,诗、宗教、思想与哲学,形而上。”他显然也在努力筑起这样的尖顶。从他的新作《去老万玉家》《爱琴海日落》《狐狸,半蹲半走》来看,更可看出萨义德所说的“艺术家毕生的美学努力臻于圆满”的晚期风格,他似大匠运斤,以无形之技挺向了高远的天空。最近出版的哲思专著《为孔子一辩:正儒与伪儒》,便是最能体现“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巅峰文本。
这部薄薄的小书,没有学究式的考据堆砌,而是以小说家的敏锐与知识分子的冷峻,直抵儒学的核心矛盾——“正儒”与“伪儒”的千年缠斗。
文化反思与现代儒学的再诠释
《为孔子一辩》是张炜多年文化探索的结晶,也是他对被异化儒学的一次深刻反思和再阐释。张炜对本土历史文化的关注,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他早年便已确立的终身命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便深度参与了当时影响深远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他的创作从来不乏人文情怀,也从不缺少历史意识。从《古船》到《为孔子一辩》,张炜始终以浪漫而不失理性的笔触关注传统,借着为天地立心的勇猛之志为往圣祛魅,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怀忧思发愤立言,唤醒被庙堂化遮蔽的文化记忆,在古老颓圮的废墟上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审美伦理。
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中,孔子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巨大存在。他由人入圣,隐而不显,像神话,甚至像幽灵一样,在普天之下游荡了两千多年。即便你从未读过半句“子曰诗云”,骨子里定也少不了因他之名而刻下的纲纪之道。然而,这些刻痕究竟有多少来自孔子?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被发明的传统”,世代相承的儒家学说也是被一代代的皇家号令、大儒大言“制造”出来的。那些言之凿凿的儒家学说究竟有多少真正来自孔子本人?张炜正是带着这种诘问,展开了他的“正儒与伪儒”之辩。以其诗人之眼、小说家之心、知识分子之思,张炜召唤孔子的归来,吁请传统儒学回到本源,沟通现代。
正儒与伪儒的文化对抗
《为孔子一辩》着力探讨传统文化内部的对抗逻辑。在张炜看来,儒家传统从来不是一条单一、纯粹的正统线路,而是一场充满内在张力的文化对抗。正儒与伪儒的分野,不仅是历史逻辑的问题,更是当代精神重构的关键所在。这一分野的存在,揭示了儒学从其诞生之初,便是一种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思想体系,它不仅要面对外部社会的变革,还必须与内部的不同解读、不同实践形式进行不断地较量。张炜如此揭示儒学被异化的本质:“知识人致力于孔子的学问,为了得到公权力的支持,经常突出解释有利于权力的一面……‘孔子’作为公权力的一部分,成为王权统治的一件法器。”而真正的儒学则应是“以‘爱’和‘爱人’为核心……为了这个目的、奔向这个结果”的生命实践。
因此,正儒是以孔子、孟子、韩愈等人为代表的敢于直面权力、坚持民本思想并保持思想独立的文化践行者。他们在历史的逆境中,以仁义、自省和批判的力量实现自我救赎。他们的思想不仅扎根于传统,更以一种不安于现状的精神,不断挑战着传统的表面化与教条化,力求让儒学展现其生命的宽广和深刻。
孔子所提倡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为本”的思想,韩愈对理学的批判,都成为了“正儒”的典范——他们的思想,不仅仅是对知识的追求,更是对社会道德、个人良知的深刻洞察,是对“人”与“道”之间关系的不断探讨。张炜通过对这些思想家的崇高定位,指明了“正儒”对于儒学的原始精神传承与弘扬的责任。所以他才特别强调:“儒学中‘最好的东西’,与世界其他民族都是相通的、相似的……人类‘最好的东西’,在不同的时空中都有一些相通处。”
与此相对,伪儒则是那些利用儒学作为维护统治工具的帮忙、帮闲甚至帮凶者。他们以“礼”“德”为名,压制个体自由、扼杀思想创新,使儒学逐渐沦为单纯的政治符号和形式主义的牢笼。张炜的批判极为尖锐:伪儒无视儒学的本真精神,只是把儒学的道德伦理工具化,用以维护专制与等级制度,甚至将个人的思想、情感与理想完全禁锢在“礼法”的框架之中。“儒学一旦落在王权手中,成为不可更易的刻板条文,就变成了最坏的东西。所以,‘伪儒’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文化桎梏。”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正儒才是儒家的本来面目,伪儒则是王权暴政的常客。
现代社会中的儒学异化与“精神返乡”
《为孔子一辩》是当代语境下的精神返乡,也是当代“作家-知识分子”重寻人文根系做出的英雄式努力。面对技术理性盛行、消费主义泛滥、公共精神日渐凋零的现代社会,张炜对传统文化的再生怀有深深的忧虑:“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孔子其实是并不重视的,甚至有些不屑。他们不相信孔子,不读且‘不以为意’。”因此他才呼唤一种“精神返乡”的力量,即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重新建立内在的文化根系和精神家园。
张炜早曾指出,现今社会中种种看似新颖的异化现象,其实都继承了古代伪儒那套以形式掩盖本质的机制:社交网络中的言语暴力、过度功利的教育体系以及遍布各处的虚假权威,都是伪儒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新生形态。“‘古典’中蕴含了‘现代’”,他认为只有回归“正儒”精神——即仁义、自由、批判与担当——我们才能逐步修复人性和文化的断裂,找回那种可以“乘桴浮于海”的精神自由。张炜笔下的孔子、徐福、陶渊明,均为“返乡者”的象征。他们以超越时空的方式,传达出一种关于归属、关于内在自由的永恒呼唤:孔子的思想不仅是历史的遗物,更是一种可以重新点燃的灯盏。
孔子归来与当代文化重建
《为孔子一辩》的非凡意义就在于,张炜以他独到的历史意识与诗人般的敏感,让庙堂化、工具化的孔夫子重返人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情感与人性温度的可爱且爱人之人。让孔子归来,找回儒学的本来面目,让古老的传统走向现代,张炜此时的言说功莫大焉。
通过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仿佛看到一位风尘仆仆的归乡者,在历史的尘烟中驾车而来。张炜盛赞那种“木车的激情”,并在书里埋下了一把令人生疑的“金属扳手”。这把扳手,既是“正儒”对伪善权威的正面回应,也是写作者对历史真相的强力一击。《为孔子一辩》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标准答案,而在于打破“伪儒”腐朽的硬壳。当张炜在书中藏下了一颗狂野之心,他所揭示的就不仅是历史的宿疾,更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他在祛魅与返魅的循环中,重新揩亮了一把力拔千钧的金属扳手。圣人无须辩,只需被理解。而张炜的诗与思,正如那把沉默的扳手,在历史的铁壁上敲出裂痕,让光透了进来。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